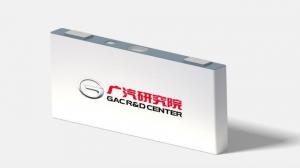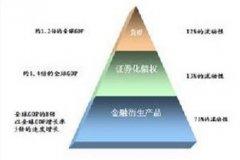□ 刘兰根
记忆中,家里的土炕上,常年放着母亲的藤编针线簸箩,六角形,枣红色,轻巧漂亮。晚上睡觉时,这个簸箩就放在窗台上。煤油灯光中,我常常盯着那个簸箩出神,一遍遍想象着簸箩里那些丰富的宝贝。
母亲的针线簸箩内总是满满当当,各种型号的钢针,大小粗细各有不同,缝被子的针最长,做夏天衣服的针最细。母亲不会绣花,她用绣花针缝出细密的针脚。走村串巷换针线的商贩摇着拨浪鼓一响,母亲就翻找闲置的鸡窝,找出几双旧布鞋、几片旧棉花套子,换回几枚钢针,几把黑白棉线。手工搓的绳子,都做好了细长的纫头,能穿过细小的针眼。纳鞋底的锥子是圆木把的,刻着几圈细纹。纳鞋底、绱鞋的针,需用小铁钳子拔出来。银白色的顶针褪去了颜色,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坑窝。在布料上画线用的粉片是薄圆形的,像一块饼干,我常偷偷拿粉片画印儿玩。王麻子剪刀锋利,裁剪布料咔嚓有声,母亲还用这把剪子给自己和我们姐妹剪头发。外面喊“磨剪子哩戗菜刀”的一来,母亲就拿上剪子去磨,花几毛钱也不心疼。菜刀却不轻易拿出去磨,因为菜刀平时切菜多,很少有肉切,不需要太锋利,母亲只把菜刀在水瓮的瓮沿上来回蹭。
松紧口主要是做布鞋用,那时有一种布鞋就叫“松紧口”。松紧带是做裤子的,如果买得够多,我就会截出一截来,跳皮筋最好了,但是我的皮筋不是都用新松紧带,我只把磨得最细的没有弹性的一截替换掉。
各种碎布头五颜六色的,最大的只有巴掌那么大,母亲挑选两块合适颜色的碎布头缝在我们的衣服上,就是两个好看的衣兜,把布头一拼接,缝在棉袄的袖子上,就是好看又干净的袖头。我把小块的剪成三角形、正方形,缝沙包,剩下的碎布条是缝毽子的好布料,那时叫“袍毽儿”。
印象中的母亲农忙时下地干活,遇有下雨天,母亲就会做针线活,母亲的簸箩里常年会放着没有纳完的鞋底。冬天里,母亲更是天天守着针线簸箩忙活。父亲是兽医,他生活节俭,身材高大,平时走村串户走路多,母亲总是不等父亲的鞋穿太旧,就做好新鞋给换掉。而父亲的袜子总是磨坏了脚后跟,他舍不得扔,就让母亲补袜子,母亲没有买到补袜子的楦子,就把袜子套在手上一点点用绣花针纫上细线缝,母亲说怕针脚大了父亲穿上会硌脚。
家里开始做生意后,母亲把针线簸箩又带到了身边,她没有更多的时间做针线活了,却依然要时不时补父亲的袜子,父亲爱穿棉线袜子,他的一双袜子总是补了又补,我劝父亲扔掉破袜子,父亲就会和我着急,他说新袜子穿着不舒服。补袜子,穿补的袜子,已成了父母的生活习惯,直到他们走完一生。
如今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的改变,不再需要那些缝缝补补,但是总是会在某一个独处的时间,或者因为一件衣服、一双鞋袜的触动,眼前再次浮现出母亲坐在针线簸箩前的身影,那些往日的回忆,一点一滴,都深深嵌在了那些细密的针脚里。
声明:本网转发此文章,旨在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资讯,所涉内容不构成投资、消费建议。文章事实如有疑问,请与有关方核实,文章观点非本网观点,仅供读者参考。